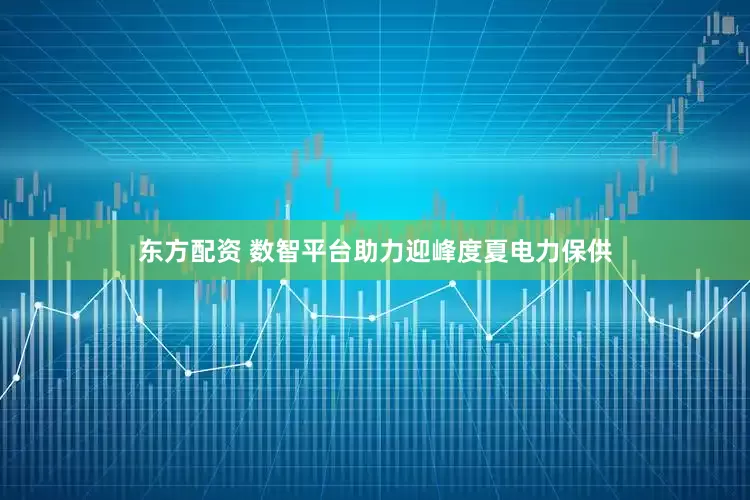沈醉一向以精明自诩交易鑫优配,但是在判断自己和“伙伴”什么时候能特赦的时候,却频频失误:他先是认为自己能出现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上,在自己第二批特赦的时候,又认为徐远举能在第三批特赦。
沈醉只失望了一年,就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徐远举则是年年失望年年望,望眼欲穿不见特赦令,在1973年把自己气死了。
同为“军统三剑客”,周养浩似乎并不像沈醉和徐远举那么希望提前特赦,我们遍翻相关回忆文章,也找不到周养浩写的交代材料,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身份被俘的周养浩似乎“躺平”了。

直到1975年全部战犯均获特赦,我们才看出周养浩的心机深沉:他之所以不积极改造,也不盼着提前出去,就是留了后手——只有这样,才能去台湾投奔蒋家父子。
周养浩机关算尽,就是每算到他特赦的时候老蒋已经病入膏肓,主事的小蒋直接给他吃了闭门羹。
周养浩虽然碰了壁,但是在自己和其他将军级特务的特赦时间上,他显然算得比较准确:既不像沈醉那样积极,也不像徐远举那样积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做过的事情也很特别,不管他如何学习改造,特赦时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沈醉认为自己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还公开通过广播和报纸命令云南特务停止活动,即使不算起义也算投诚,第一批特赦就应该有他。
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后,沈醉是很不满的,即将离开的杜聿明安慰他的时候,他居然急眼了:“杜聿明在和我分手时,已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所以他走出寝室门,一大群人争着和他握手,他看我没有伸出手来,便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泄气,也没有理由泄气,既有第一批肯定会有第二第三批,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好好再争取一下吧!我在外面等候见你。’我一听这话立刻反感异常,便气愤愤地说:‘我还不合特赦标准,当然我比不上你!’(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经杜聿明开解,沈醉才想起自己关押时间还不到十年,这才对杜聿明的严谨表示敬佩,同时也对自己的特赦不抱希望,所以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会去审议的时候,沈醉先是兴奋,然后出现了误判:“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没有干特务的,别处特赦的也没有干特务的交易鑫优配,我便肯定第二批不会有我。”
沈醉是这样分析的:第一批特赦人员共有三十三名,其中十名出自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十人都是高级军官,战场厮杀没有个人恩怨,所以特赦早一点很正常,而沈醉从十八岁就入行当特务,被他逮捕、杀害、迫害过的人不上万也过千,他承认自己1949年在昆明就曾主持逮捕过近五百人:“现在正在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许多人中我也迫害过,有的甚至打骂过,还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
沈醉以己度人,认为会被报复,结果第二批特赦名单一出来,他再次傻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二批喜有我,从此做新人。”
欣喜若狂的沈醉还不忘“鼓励”他的“老朋友”徐远举:“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词,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

为什么让徐远举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笔者没有从相关资料中找到答案,但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后,第一个跳脚大叫的确实是徐远举,而且徐远举的喊叫,还引起了很多待特赦战犯的“共鸣”。
徐远举不像沈醉那样听人劝,甚至连自己的关押时间都没计算就发牢骚,果然跟他的“猛子”绰号十分匹配——当年特赦有两个必备条件:其一,确已改恶从善;其二,改造已满十年。徐远举有没有改造好暂且不提,他跟沈醉一样,在第一批特赦时还差几个月满十年,却是无法改变的。
我们翻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和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能找到沈醉和徐远举近乎交代材料的回忆文章,这说明沈徐二人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如果说沈醉的文章还有些遮遮掩掩,那么徐远举的《自供状》则毫不掩饰:“1948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徐远举能写出“国民党反动派”六个字,说明他已经跟蒋家父子彻底划清了界限,这六个字,在沈醉的五本回忆录中,也仅仅出现过两次而已。

徐远举一直以为自己能提前特赦,沈醉似乎也有同感,而不像沈醉那样积极,也不像徐远举那样着急的周养浩则心中有数:同样是军统(保密局)特务,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交出”四个少将特务(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的沈醉可能提前特赦,郭旭也可能提前特赦,但他和徐远举以及其他大区区长、省站站长、总部少将处长或专员,是很难提前特赦的。
郭旭是“经理处”处长,跟沈醉当“总务处长”时的工作性质差不多,手上血债不像徐远举周养浩那么多,而且郭、沈二人都比较精明,知道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就连文笔也比其他行动特务好一些,我们翻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也能找到郭旭写的《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杀》《重庆、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与大屠杀》、《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署名为沈醉、郭旭),此外郭旭还写了《孔祥熙其人其事》、《戴笠及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在将军级特务战犯中,郭旭的“作品”数量仅次于沈醉,所以沈醉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郭旭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
特务出身的特务,如果不是改造特别积极,就几乎不可能在前几批特赦,如果是血债累累,那么即使改造也比较积极,写的材料也比较多,特赦还是不那么容易,这一点徐远举不不知道,周养浩却十分清楚,所以他的态度一开始是又臭又硬吗,后来是“随大流”。

手上沾了太多鲜血还想早些出去,徐远举比较“天真”,而周养浩则比较狡猾,他“不声不响”给自己留了后路,在这方面,他确实比徐远举“高明”——作为《红岩》中徐鹏飞、沈养斋、严醉的历史原型,徐远举和周养浩在书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严醉(沈醉)还有一丝天良未泯,所以沈醉能提前出去,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就只能“耗着”了。
即使仅以《红岩》为依据,我们也能发现徐远举周养浩罪无可赦,沈醉这个跑腿学舌的还没有坏透腔。
就连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自己罪过不小,徐远举周养浩的罪过更大:“我在昆明一次抓过四百多人,秘密杀掉了几个我认为是企图打进云南省站的参训班的学生。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内所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甚至连因违反纪律关在里面的军统特务,都一个不留地杀掉了。周养浩在重庆担任保防处长时,把该处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都杀了,在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主任时,杀过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先,以及打进军统的共产党员张蔚林等上百人。”

如果改造积极,就能把累累血债一笔勾销,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同,这一点周养浩十分清楚,所以他认定自己和徐远举不可能像沈醉郭旭那样通过撰写揭发材料获得特赦。
事实也正如周养浩预料的那样,他跟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局本部第一处少将处长鲍志鸿、训练处少将处长郑锡麟、少将专员段克文,以及河南站站长岳烛远、广东站站长何崇校、广西站站长谢代生、湖南站站长黄庚永、浙江站站长章微寒等人,都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特赦的。
擢发难数,罄竹难书。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徐远举、周养浩等将军级特务的罪行一点都不为过,所以徐远举想提前特赦只能是梦想,周养浩也不会认为自己特赦过晚,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沈醉该不该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如果徐远举不是在1973年病死,他是不是也得等到1975年才能跟周养浩一起特赦?
鸿岳资本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